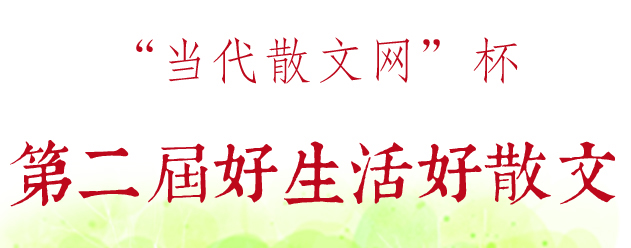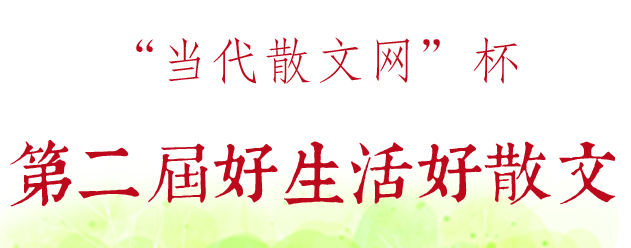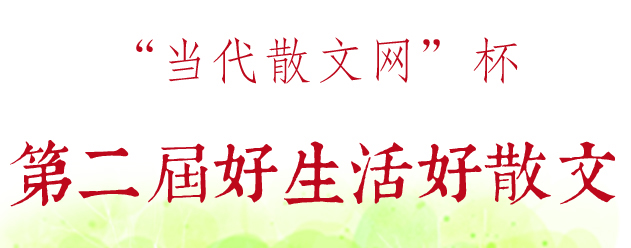-
李铁峰:故园又到叶落时
秋天的每一片落叶,始于萌芽终于枯黄,但都是在最好的季节绽放了最美的风采。站在办公楼窗口,举目看到通衢大道两边的树木在秋风里摇落,想起故乡也到了落叶飘零的季节,巍巍青山披上金黄的新装,错落的红瓦粉墙村居在山坳里冒起缕缕炊烟,小河蜿蜒而下,比盛夏瘦了许多,芦荻萧萧飞似雪,都静默成夕阳下独特的风景。想起上午故乡大哥那个电话,他在整理家谱,让我提供临沂分支的家族序列,我特别叮嘱他给烈士四爷爷专门列出一栏内容,那就是我无意中从中华英烈网查到的信息,“烈士李克堂,生于1925年6月,牺牲于1945年9月,所在部队是鲁中特务团。”他仅仅活了20岁,就永远沉睡在临沂大地上,在故乡河边那一座刻有“烈士李克堂”墓碑的坟墓,成了家族唯一的哀思寄托。生命的意义,是我始终思考的主题。记得在童年时,冬天是农村闲暇的时光,一座草房子里,家族的几代人围着一个火炉剥花生或玉米,那时爷爷们很多都健在,我曾经问起他们在抗战年代支援主力部队阻击日寇的事迹,在他们嘴里都是轻描淡写的话语。我曾问道:“那时候你们怕不怕被杀头?”他们笑哈哈地说:“谁不怕被杀头,谁的头也不是地里的韭菜,还能割了再长出来?”“明知有杀头危险,你们为什么还要积极入党,一分钱不挣也拼死去参加战斗,你们很多仅仅是一个党员身份。”我很好奇。他们好像面对怪物一样看着我,瞬间又笑了,说道:“这土地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吧,凭什么让他们占去,我们是怕杀头,但他们
2020-12-12
阅读详情
-
赵廷河:行走的野草
在城市里住得久了,对菜地几近淡忘了。惊蛰那天下班回家,妻高兴地对我说:“开画室的大山表弟怕院子里长草,让我们去开一片荒地种菜。”我惊喜地说:“那太好了!”于是,我成为这片菜地里的常客。看到妻整的六个菜畦平平整整,干干净净,很是喜欢。她一有空就在菜地里忙碌,翻地、施肥、播种、锄草、搭架、浇水等,忙得不亦乐乎。不久,她种的黄瓜开花了,偷偷绕过手掌大的叶子,高擎在阳光下,呈现出金灿灿的黄,是在招蜂引蝶呢;苦瓜也开始显山露水,沟沟坎坎,都在膨胀,一刻也不停地忙着扩张自己的地盘;小葱则拱出地面,挤眉弄眼,芽尖的泥土还没来得及抖落干净……今年麦收刚过,妻就让我到菜地里去锄草。我下班后到菜地一看,除了种的各种蔬菜长势旺盛外,那菜畦里、畦埂上突然间长满了绿油油的杂草。有毛谷英、灰灰菜、蒲公英、车前草、马齿苋、云星菜……这些都是我最熟悉不过的野草野菜呀。我一见到它们,就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感到十分亲切、自然、兴奋。你看,野草的根深深扎进土地,通过叶面来进行光合作用。它是最能吸纳天地之灵气的。对此,维生素多蕴含在云星菜、马齿苋等野菜当中。小时候,我经常放牛、放羊。牛羊通过青草来摄取营养,人们再通过牛羊的肉来摄取营养,然后,牛羊和人的粪便施到田地里,又可作为肥料给青草带去营养。这个循环过程,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实际上,这可是一个十分完整而巧妙的轮回。野草在这样的一个轮回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2020-12-12
阅读详情
-
王旭虹:寂静的小路
这条路,于我来说是隐秘而静寂的。我常常在每一个清晨或者傍晚,独自一人踏上这条小路,享受片刻的宁静。春天的时候,脚下尽是松松软软的泥土,偶尔有一只小鸟儿好奇地从面前飞过,落到树枝上,再扭过头来叽叽喳喳地和我打打招呼,或许,它在说:“你好你好!”或许,它在奇怪,这么乍暖还寒的春天的早晨,这个人来干啥啊,可以吃的食物已经寥寥可数,树梢上挂着的果子也没有几颗了。我看到的鸟儿的状态,大多都是一只一只的在飞翔,觅食,跳跃,在树林中显得孤寂而落寞。偶尔碰到两只相伴翩翩飞翔的小鸟儿,小路上的林子里霎时活泼起来,但见那两只叽叽喳喳飞仰俯合的小精灵,忽高忽低,忽前忽后,忽而露出肚皮,忽而啄着羽毛,像两个活泼烂漫的孩子,享受着两小无猜的亲昵和快乐。这个时候,整条小路,整个林子都跳跃着甜蜜的音符。这只是偶然。最常态的还是零零落落的一只一只鸟儿,各自觅食,各自梳理自己的羽毛,神态悠闲地踱来踱去。大概孤独是人间常态吧!纵使鸟儿也是如此!如同眼前的一排排树,虽然天天、月月、年年站在一起,却也不是相互箍匝捆绑,它们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让空气、阳光、风儿……无拘地照进来,吹进来,以便足够的养分来维持生长。所以它们永远保持昂扬的状态。因为自由而更加快乐,因为陪伴而安详幸福!绚烂多彩的夏天,荷尔蒙弥漫到整个空气里。小路依然是宁静的。不过,这时的宁静是湿润而朦胧的。偶尔有三三两两的恋人走过,便觉有一缕香风飘过。人世间的情爱
2020-12-11
阅读详情
-
吴振亚:怀念爷爷
爷爷过世都三十年了。每当想起他的音容像貌,我的内心总是会感慨万千。做为长孙,我是爷爷最疼爱的那个孙子。爷爷过世后的许多年,我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境与情节都大同小异。小时候,我们大家族住在一条巷子口的最深处,我总是梦见爷爷做完了晚饭,一个人站在院子,双手插着腰,向巷子口张望。等候着家人回来吃饭。爷爷张望的背影是那样的伟岸和高大,令我久久难以忘怀。爷爷有一副欣长的身材,宋瓷一般细致超脱的外观,行走如风,坐则无声无息。他很少找人交流,似乎很难接近,很难将气氛激活。开群众大会,他一般坐在不起眼的角落,像一名小学生,坐得端端正正,听得聚精会神,从不说小话,只是默默的吸着他的烟。爷爷退休前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经常会抱回一些乱七八糟的奖状和奖品。爷爷脾气不好,体会最深的要数我那唯唯诺诺的奶奶了,可惜她也不在人世。有时表面看爷爷是一种烟气袅绕的静态,或许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景观。可是在烟层的下面,是一张可怖的脸,只需一点火星,他的火便要发作。他的火是瞬间发生的,卷地风雷,乍起乍落。奶奶经常会被爷爷的狂风吹倒,几次险些丧命。然而爷爷在世的时候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得九十九。这份预言在奶奶身上得到了证明。奶奶活了九十九岁才撒手人寰。爷爷年轻的时候是这一带有名的木匠。在生活水准低下,茅屋盛行的时代,他的一部份日子是在屋顶度过的。爷爷去做事,极好招待,他不吃荤,主人端出一碗有颜有色的青菜,他就喜欢。那青瓷小
2020-12-11
阅读详情
-
安安:和娘行走在深秋里
一如果娘的第一次住院让我感觉像一次旅游,那么出院一天之后的第二次住院,才让我们真正的提高警惕。而接二连三的第四次住院,此时的娘犹如独立行走在风口浪尖,变得无助猜疑,变得不知所措,变得小心翼翼。娘每一次都报喜不报忧,她怕这个远嫁的女儿担心,而愚昧的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娘有所好转。此时孱弱不堪的娘,眼眶发黑,头发花白,脸庞消瘦。娘有气无力地说:“这几天背上火烧火燎的难受,真是光有出的气了!”我懂娘,不是万不得已娘不会在我的面前承认疼。这次,娘是真疼了!我不想在娘的面前表现出自己软弱,但眼泪毅然以最后的决绝,挣脱了我的眼眶。我掀开娘的后背,沾上凉水为娘按摩。娘的背很薄,清晰可见的骨架连接整个身体,经不起我寸指之间的力量,只为缓解片刻的疼痛。第二天,2020年10月8日,娘第四次住进市人民医院。国庆之后的医院,仍保留着吐露芬芳的鲜花,但五彩缤纷我和娘都无心顾及。我用并不灵光的轮椅推着娘,穿梭在CT室、磁共振检查室、心脏彩超检查室的拥挤人潮中。被病痛纠缠的娘已经不像利利落落的娘了。她随意穿着花棉袄、花棉裤,不合适宜地围了一块白头巾,刘海那缕因过道强劲的风而东倒西歪的头发,倔强地挺立着。我们穿梭在各个楼区之间,对于帮我们揭开厚重的防风布帘子,或者帮助我们按电梯,甚至欠欠身腾出我们一席之地的陌生人,娘总是表现出十分的友好,弱弱地说一声:“谢谢呀!”娘的土话浓得化不开,但娘仍旧用简单的礼节,表达自己
2020-12-10
阅读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