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种果实》由作家李志明著,诗人王夫刚先生作序,全书共分村庄的根或者背面、唯有泥土和黑暗值得拥抱、争先恐后替他活着三小辑,本书封面采用进口特种纸加烫黑工艺,外加副封,封面简洁大方、格调高雅,该书采用14cmX21cn,精心印刷,由济南海东文化设计制作、印刷,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王夫刚
1976年,博尔赫斯先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参加自己的生平与创作对话活动,巴恩斯通问了一个中国诗人特感兴趣的问题:“是你去找诗呢,还是诗来找你?”博尔赫斯回答说,“我要说是诗来找我,而且甚至小说也来找我。我的脑子大了,就得减轻它的负担,而减轻负担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东西写出来。”高龄且失明已久的博尔赫斯谦逊,风趣,博学,侃侃而谈,温文尔雅,他晚年失去了阅读的权利,自己却像一座被阅读的图书馆渐渐成为文学的新坐标横亘于咫尺天涯的地平线。40多年以后,我索居京华,在一个不断抻长但禁止四处走动的怪异的春天,怀着老友的心情阅读诗人李志明即将出版的诗集《第六种果实》——我可能是这本诗集的第一个读者——忽然想起博尔赫斯愿意公开接受的这个非处方诗歌写作标准。“诗来找我”的对立存在并非“诗不来找我”,而是“我去找诗”,换算成中国诗人更为耳熟能详的汉语阐释,谓之“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显然,“诗来找我”是一种主动性褒奖事关心灵的再启发,而“我去找诗”则是另一种主动性褒奖止步于汉字的纸上谈兵——写作者如果赞成“我去找诗”属于诗歌写作的初级状态,他就有可能领取甚至已经领取“诗来找我”的更高诗歌写作福利。诗集《第六种果实》究竟是“诗来找我”替志明承担大脑的减负责任,还是“我去找诗”跟他达成了纸上的绥靖协议?我给出的判断倾向于前者,虽然志明的文本在完整的谱系建设和合理的语言去弊上还有着过去承载不了的提升空间,但在诗集《第六种果实》中,白云停下,闪电破灭,飞蛾扑火,梦有高潮,河水越来越瘦,沉默不语的石头冒出汗水,墓地里的野花惊扰沉睡的亡灵,即将被拆迁的房屋演绎“书法”的游戏,发誓做一棵树的人曾经热衷于打鸟捉鸟,泥土与黑暗的拥抱者希望人间回荡着从未有过的充盈……众多不请自来的诗篇,也是命中注定的诗篇,它们历经光阴的善意提醒和灵魂的自然分娩,终以“诗来找我”的方式声援了“诗来找我”的博尔赫斯先生。需要注意的是,“诗来找我”兼有灵感的部分功能,但若把“诗来找我”完全视为写作的灵感造访,在我看来也不能算作准确的表述。
2
为了方便我从济南回老家五莲,山东省在十几年前修建了济青高速南线,中途的沂源县成为我的往来必经之地。每次路过,我要么在高速服务区稍事休息,一边喝水,抽烟,一边用地理老师的目光巡视寂静山河,偷梁换柱地想起多年以前布恩迪亚上校被父亲带着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要么直接下了高速,去到高速路边的沂源县城,见见志明,聊聊诗歌——对于生活而言,这种无主题变奏仿佛生活的意外,对于诗歌而言,则算得上一种听命内心的行为艺术不需要搭建临时舞台。沂源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号称“山东屋脊”,著名的沂源猿人四五十万年前就在这里茹毛饮血,耐心等待着钻燧取火的文明照亮未来的岁月,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是志明的家乡,是志明不可选择的人生起点和几乎不可选择的生命归宿。早年志明出过一本诗集,叫做《流水穿过菜园》,流水穿过的菜园实为流水穿过的菜园村,志明的童年、少年以及中年回忆寄托于此;早年志明还出过一本诗集,叫做《穿西装的土豆》,意会的读者自能分辨,穿西装的土豆跟服饰无关,跟餐桌也无关,穿西装的土豆与其说是志明的个体诗意自嘲,不如说是一代人的局部命运向古老的诗经或者伟大的史记致敬的证据。从《流水穿过菜园》到《穿西装的土豆》再到《第六种果实》,志明尝试用三本阶段呈现的诗集诠释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关系:不曾离开,不言归来,所有藕断丝连的梦都曾沿着沂河源头寻找精神的归宿并且所获可见。祝贺志明,在可控的命运中实践了自己可控的诗歌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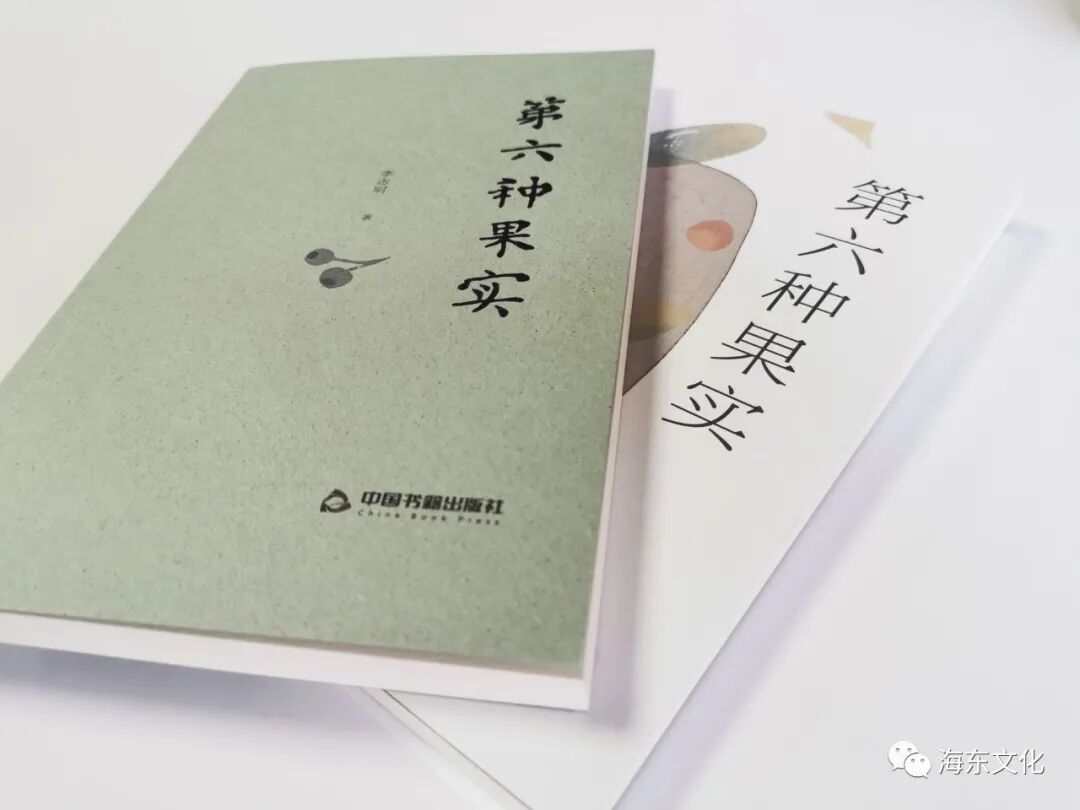 读完诗集《第六种果实》,我意识到,通过微信或者邮件向志明表示简洁祝贺,已然不是我们之间最好的互动方式。时代在高速路上提速,在互联网横冲直撞,但诗歌尚未做好投诚准备,也不打算无条件接受时代的提速要求和横冲直撞的教育方式——面对命令般袭来的潮流(泥沙俱下的即时诱惑),诗歌有时极力抗拒,有时显得漫不经心,而志明和我等,之所以持续着从前的情怀,归根结底是把赞成票投给了诗歌的垄断性自信:她看谁一眼,谁就当心存感激。江湖有诗尝曰“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按照这个规矩,志明的《第六种果实》允许是一本诗集有人阅读,也允许是一片星空无人仰望,所有来自形式主义的现实褒贬,都可能等同于对心灵私设公堂并把虚拟拷问写入戴着面具的判决书。记者出身的马尔克斯名满天下以后曾经试图重操旧业,结果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新闻本身,被博尔赫斯视为英雄的爱默生则有警告说,“让我们当心吧,生活本身也许会变成一段长长的引文。”这里不妨借用一下:“让我们当心吧,诗歌本身也许会变成一段长长的引文。”我虽然优先阅读了诗集《第六种果实》,却不认为跟它保持条分缕析的关系属于最佳选择——这首诗很好,那首诗不够好,另外一首诗不够好也不够不好——如果阅读不慎变成诸如此类“长长的引文”,完整的阅读体验就将变得支离破碎。事实上,通过一首诗接触一个截面呈现的诗人和通过一本诗集剖析一个纵深开掘的诗人,其合理性和差异价值从来都是殊途一归而又两两不同,诚如现在,我向诸位推荐诗集《第六种果实》,并非始于文本解读,而是怀着排斥文本解读的另外一种心情,虽然我手里拿着免费使用的放大镜,也从不拒绝在引经据典的课堂上为学院派的同行们点赞。上述观点,其实有更为简明的表述:评论家的二手生活因为引号超标而令人难以忍受。批评不能解决写作的问题,同理,表扬也不能。这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几乎每周都要阅读大量诗歌,那些勇气可嘉的写作者,既没有“诗来找我”的幸遇,也缺乏“我去找诗”的基准历练,仅凭借令人叹为观止的热情(或者欲望)取悦诗歌,示爱诗歌,及至难为诗歌,向诗歌索取诗歌兑现不了的不可描述的附属奖励——在很多人眼里,写作无非一个不设门槛的彩票站,而“诗是吾家事”刚好作为一种不计成本的赌注,随时准备迎来与“人传世上情”无关的中奖结果,从而满足“我去找诗”的最低消费。我有时对自己充满厌倦般的同情,那些简单、粗鄙、不值一提的诗篇,居然能够间接命令我既愤愤不平,又在无效阅读的泥淖里保持匪夷所思的淡定。值得庆幸的是,无效阅读所衍生的教训促使我愈加清醒、谨慎和自重(我可不想在诗歌那里成为被怜悯的对象);更值得庆幸的是,我跟志明谈论泥淖里的寂寞挣扎和洁身自爱,志明感同身受(我理解为志明同样不想在诗歌那里成为被怜悯的对象)。这种貌似巧合的心境,其实来之不易,志明和我生于相似的农家,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走了很多年,走了很多路,经历了写作的漫长考验和人性的现实主义审查,能够不经试探而亮出不谋而合的诗歌底牌,也算人海茫茫,别来无恙。所以,当我含蓄地抱怨通过文本的单边解读方式获取诗集《第六种果实》的谜底是一种变相的“阅读管制”而志明同样含蓄地予以赞成时,我竟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评论家的引号超标的二手生活再一次失去了逼我就范的机会。
读完诗集《第六种果实》,我意识到,通过微信或者邮件向志明表示简洁祝贺,已然不是我们之间最好的互动方式。时代在高速路上提速,在互联网横冲直撞,但诗歌尚未做好投诚准备,也不打算无条件接受时代的提速要求和横冲直撞的教育方式——面对命令般袭来的潮流(泥沙俱下的即时诱惑),诗歌有时极力抗拒,有时显得漫不经心,而志明和我等,之所以持续着从前的情怀,归根结底是把赞成票投给了诗歌的垄断性自信:她看谁一眼,谁就当心存感激。江湖有诗尝曰“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按照这个规矩,志明的《第六种果实》允许是一本诗集有人阅读,也允许是一片星空无人仰望,所有来自形式主义的现实褒贬,都可能等同于对心灵私设公堂并把虚拟拷问写入戴着面具的判决书。记者出身的马尔克斯名满天下以后曾经试图重操旧业,结果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新闻本身,被博尔赫斯视为英雄的爱默生则有警告说,“让我们当心吧,生活本身也许会变成一段长长的引文。”这里不妨借用一下:“让我们当心吧,诗歌本身也许会变成一段长长的引文。”我虽然优先阅读了诗集《第六种果实》,却不认为跟它保持条分缕析的关系属于最佳选择——这首诗很好,那首诗不够好,另外一首诗不够好也不够不好——如果阅读不慎变成诸如此类“长长的引文”,完整的阅读体验就将变得支离破碎。事实上,通过一首诗接触一个截面呈现的诗人和通过一本诗集剖析一个纵深开掘的诗人,其合理性和差异价值从来都是殊途一归而又两两不同,诚如现在,我向诸位推荐诗集《第六种果实》,并非始于文本解读,而是怀着排斥文本解读的另外一种心情,虽然我手里拿着免费使用的放大镜,也从不拒绝在引经据典的课堂上为学院派的同行们点赞。上述观点,其实有更为简明的表述:评论家的二手生活因为引号超标而令人难以忍受。批评不能解决写作的问题,同理,表扬也不能。这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几乎每周都要阅读大量诗歌,那些勇气可嘉的写作者,既没有“诗来找我”的幸遇,也缺乏“我去找诗”的基准历练,仅凭借令人叹为观止的热情(或者欲望)取悦诗歌,示爱诗歌,及至难为诗歌,向诗歌索取诗歌兑现不了的不可描述的附属奖励——在很多人眼里,写作无非一个不设门槛的彩票站,而“诗是吾家事”刚好作为一种不计成本的赌注,随时准备迎来与“人传世上情”无关的中奖结果,从而满足“我去找诗”的最低消费。我有时对自己充满厌倦般的同情,那些简单、粗鄙、不值一提的诗篇,居然能够间接命令我既愤愤不平,又在无效阅读的泥淖里保持匪夷所思的淡定。值得庆幸的是,无效阅读所衍生的教训促使我愈加清醒、谨慎和自重(我可不想在诗歌那里成为被怜悯的对象);更值得庆幸的是,我跟志明谈论泥淖里的寂寞挣扎和洁身自爱,志明感同身受(我理解为志明同样不想在诗歌那里成为被怜悯的对象)。这种貌似巧合的心境,其实来之不易,志明和我生于相似的农家,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走了很多年,走了很多路,经历了写作的漫长考验和人性的现实主义审查,能够不经试探而亮出不谋而合的诗歌底牌,也算人海茫茫,别来无恙。所以,当我含蓄地抱怨通过文本的单边解读方式获取诗集《第六种果实》的谜底是一种变相的“阅读管制”而志明同样含蓄地予以赞成时,我竟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评论家的引号超标的二手生活再一次失去了逼我就范的机会。 弗罗斯特发明了在白桦树枝上荡秋千的记忆,阿米亥发明了一个导游,证明古罗马时期的一个拱门曾经沿着他的脑袋右边移动和存在,现在,志明发明了第六种果实,告诉我们在爱恨交加的沂蒙山区,为什么绵延的爱总是多于断崖之恨:第六种果实最初是一个比喻,后来成为一首诗的题目,再后来,晋升为一本诗集的名字占据着封面的醒目位置。在这首简洁的诗中,志明用简洁的手法讲述一个简洁的故事:技术员在一棵树上神奇地嫁接出了五种果实,他的红脸膛,被诗人情不自禁地比喻为第六种果实。熟悉志明的人都知道,一直以来,家乡赞美诗和改良的家乡赞美诗在他的写作中始终占有骄傲的份额,他有不少文本,早在这首诗之前就担起了这首诗的责任。这位菜园村的游子,即便坐到沂源县的主席台上,也不曾忘记跟他最为熟悉的人和事物打招呼——这当然不是志明心血来潮,临场发挥,而是储存在骨子里的乡情永恒地教育着他。被比喻的技术员,也许是志明的发小邻居,也许是志明的早年同事,也许是跟志明擦肩而过的街头身影,也许就是志明自己,或者志明虚构的自己,通过发明一种果实让失联的青春之歌回到当下生活,介入情感建设。彼时激情,此际余烬,志明本想通过写作安慰回首岁月时的感慨,一不小心贡献了一个大于感慨的道理,而我关心的问题也许跟你一样:被比喻的技术员,有没有读过《第六种果实》这首诗?有没有读过《第六种果实》这本诗集?做了父母的人谈论父母,没有做父母的人谈论父母,不在同一频道;做了父母的诗人写一首诗献给父母,没有做父母的诗人怀着理解父母的心情写一首诗献给父母,分属两种甘苦自知的爱。如果一个做了父母的诗人说,他不允许父母走入他的诗篇,那么也请允许我反驳,这样的诗人是不可信的,而不可信,是一种极其糟糕的评价。很荣幸,志明和我,都已做二分之一的父母很多年(也只能做二分之一的父母啦),都曾写下不止一首的诗篇感激或者怀念我们的父母。在诗集《第六种果实》中,志明的父母不辞辛苦,至少出场十几次,让志明的十几首诗师出有名——年迈的母亲依旧自己生火做饭,依旧仔细检查了每一块木柴才肯放进燃烧的灶膛,不是怜惜木柴,而是担心枯木生虫来不及火里逃生(爱的细节如此生动而意味深长);生前因病输掉了半个身体的父亲已经不能再给志明提供长辈的教诲,却在去世后意外盘活了“争先恐后”这个他也许从未使用过的词汇:毕生忙碌于除草保苗的倔强老头,欣然接受坟头青草争先恐后替他活着的事实,并把这个事实视为最好的遗嘱留在人间。诗人与父母的关系,既是一种不容商榷的血缘传承,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学现象;诗人与子女的关系呢?肯定也是一种血缘传承,但未必需要具体的诗篇从中传达爱的信息:起码在这本诗集中,已做二分之一的父母很多年的志明,有意无意地禁止了自己的孩子走入自己的写作,成为诗的主角(哪怕是一首诗)。依据我的写作经历判断——我在儿子上学之后便不好意思再写诗给他,而去世的父亲却一再构成及至满足了我的私有怀念,志明的心情,或亦如此。这是一个平衡而有趣的悖论,孩子一面在父母的羽翼下获取更多呵护,一面像山巅上的树木跃跃欲试,一颗挣脱群山的心哪里还用得着把父辈专门写下的诗篇当作成长的礼物予以珍惜。在被呵护和付出呵护之间,诗人承上启下,诗人的写作本能地首选前者,面对父母,感恩父母,致敬父母,为父母立传,也是人伦常情,理所当然(马尔克斯认为,父母是隔在我们跟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至于孩子们局部缺席长辈的文本,无非一种隐形的内敛之爱暂且寄存于更为具体和可视的生活中,不会产生厚此薄彼的隐忧——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写诗的父亲可以作为成长的坐标,或者作为成长的坐标被成长本身轻描淡写地忽略。因此,我在诗集《第六种果实》中读到“世界如此简单/就像这个寂静的午后”“对美的认识/我们不比一只羊更有见地”以及“神也不必出现/神也有多余的时候”等诗句,从来没有质疑过志明是不是以答非所问的方式冒犯了亲爱的读者。
弗罗斯特发明了在白桦树枝上荡秋千的记忆,阿米亥发明了一个导游,证明古罗马时期的一个拱门曾经沿着他的脑袋右边移动和存在,现在,志明发明了第六种果实,告诉我们在爱恨交加的沂蒙山区,为什么绵延的爱总是多于断崖之恨:第六种果实最初是一个比喻,后来成为一首诗的题目,再后来,晋升为一本诗集的名字占据着封面的醒目位置。在这首简洁的诗中,志明用简洁的手法讲述一个简洁的故事:技术员在一棵树上神奇地嫁接出了五种果实,他的红脸膛,被诗人情不自禁地比喻为第六种果实。熟悉志明的人都知道,一直以来,家乡赞美诗和改良的家乡赞美诗在他的写作中始终占有骄傲的份额,他有不少文本,早在这首诗之前就担起了这首诗的责任。这位菜园村的游子,即便坐到沂源县的主席台上,也不曾忘记跟他最为熟悉的人和事物打招呼——这当然不是志明心血来潮,临场发挥,而是储存在骨子里的乡情永恒地教育着他。被比喻的技术员,也许是志明的发小邻居,也许是志明的早年同事,也许是跟志明擦肩而过的街头身影,也许就是志明自己,或者志明虚构的自己,通过发明一种果实让失联的青春之歌回到当下生活,介入情感建设。彼时激情,此际余烬,志明本想通过写作安慰回首岁月时的感慨,一不小心贡献了一个大于感慨的道理,而我关心的问题也许跟你一样:被比喻的技术员,有没有读过《第六种果实》这首诗?有没有读过《第六种果实》这本诗集?做了父母的人谈论父母,没有做父母的人谈论父母,不在同一频道;做了父母的诗人写一首诗献给父母,没有做父母的诗人怀着理解父母的心情写一首诗献给父母,分属两种甘苦自知的爱。如果一个做了父母的诗人说,他不允许父母走入他的诗篇,那么也请允许我反驳,这样的诗人是不可信的,而不可信,是一种极其糟糕的评价。很荣幸,志明和我,都已做二分之一的父母很多年(也只能做二分之一的父母啦),都曾写下不止一首的诗篇感激或者怀念我们的父母。在诗集《第六种果实》中,志明的父母不辞辛苦,至少出场十几次,让志明的十几首诗师出有名——年迈的母亲依旧自己生火做饭,依旧仔细检查了每一块木柴才肯放进燃烧的灶膛,不是怜惜木柴,而是担心枯木生虫来不及火里逃生(爱的细节如此生动而意味深长);生前因病输掉了半个身体的父亲已经不能再给志明提供长辈的教诲,却在去世后意外盘活了“争先恐后”这个他也许从未使用过的词汇:毕生忙碌于除草保苗的倔强老头,欣然接受坟头青草争先恐后替他活着的事实,并把这个事实视为最好的遗嘱留在人间。诗人与父母的关系,既是一种不容商榷的血缘传承,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学现象;诗人与子女的关系呢?肯定也是一种血缘传承,但未必需要具体的诗篇从中传达爱的信息:起码在这本诗集中,已做二分之一的父母很多年的志明,有意无意地禁止了自己的孩子走入自己的写作,成为诗的主角(哪怕是一首诗)。依据我的写作经历判断——我在儿子上学之后便不好意思再写诗给他,而去世的父亲却一再构成及至满足了我的私有怀念,志明的心情,或亦如此。这是一个平衡而有趣的悖论,孩子一面在父母的羽翼下获取更多呵护,一面像山巅上的树木跃跃欲试,一颗挣脱群山的心哪里还用得着把父辈专门写下的诗篇当作成长的礼物予以珍惜。在被呵护和付出呵护之间,诗人承上启下,诗人的写作本能地首选前者,面对父母,感恩父母,致敬父母,为父母立传,也是人伦常情,理所当然(马尔克斯认为,父母是隔在我们跟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至于孩子们局部缺席长辈的文本,无非一种隐形的内敛之爱暂且寄存于更为具体和可视的生活中,不会产生厚此薄彼的隐忧——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写诗的父亲可以作为成长的坐标,或者作为成长的坐标被成长本身轻描淡写地忽略。因此,我在诗集《第六种果实》中读到“世界如此简单/就像这个寂静的午后”“对美的认识/我们不比一只羊更有见地”以及“神也不必出现/神也有多余的时候”等诗句,从来没有质疑过志明是不是以答非所问的方式冒犯了亲爱的读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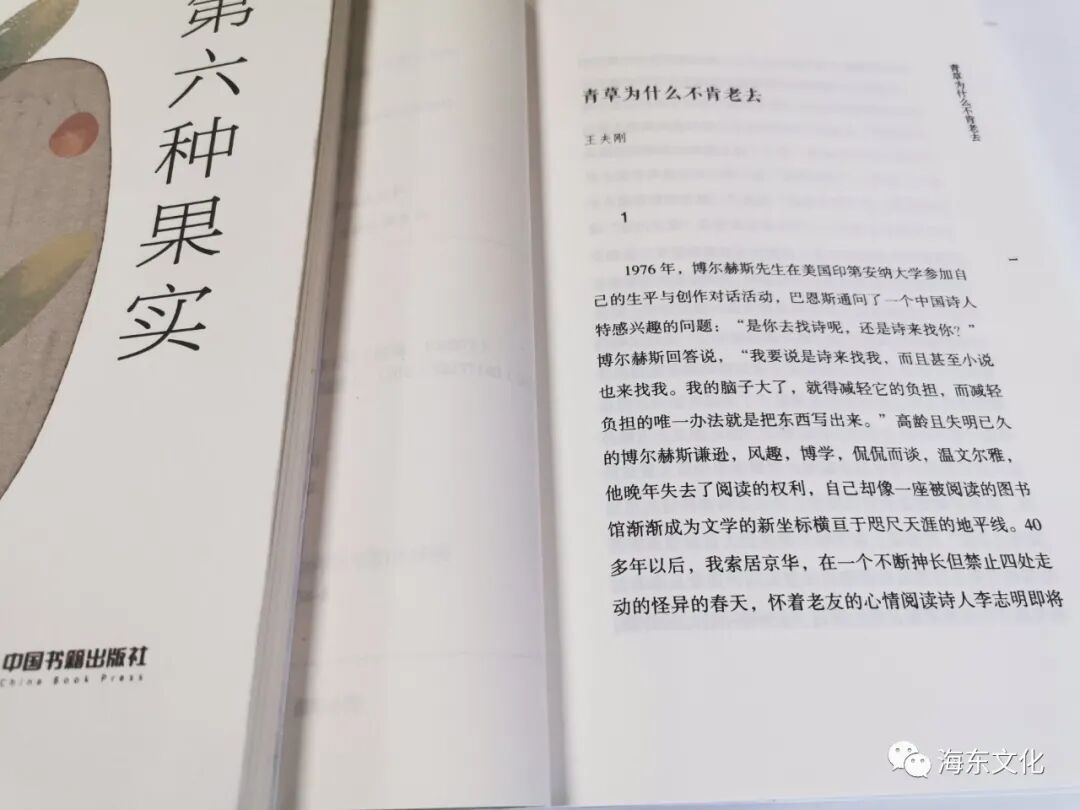 多克托罗说,好的作品之于读者,不是正在下雨的事实,而是被雨淋的感觉——很早以前我读志明的作品,就曾体会过这种被雨淋的感觉。志明写有一首短诗《一个民工在打手机》,简陋的工棚里,一个年轻民工躺在简陋的小床上打电话,结尾是:“汗渍藏起了他的表情/机器的轰鸣掩盖了他的声音/我只看到两只伸出床外的大脚丫/像两只鸟,高兴地抖动”。如果我们没有去过深刻影响了生活的建筑工地,如果我们没有亲人朋友做建筑工人,就很难理解天地间抖动的两只大脚丫所蕴含的尘埃里的喜悦;同样,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份尘埃里的喜悦,也就很难参与到这首诗所生发的被雨淋的感觉。诸如此类的作品,志明写有不少,细心的阅读者在诗集《第六种果实》中也会常遇——《树荫悄悄出卖了他》《父亲拔草》《一棵开花的树》等诗作,就跟这种尘埃里的喜悦有着和光同尘、相互照应的关系。我有时审问自己,为什么对这种强调画面感的清晰之诗如此印象深刻,我想,不是它们承载的思想改变了我的阅读标准,而是诗人赋予它们的生活意趣以及由此产生的真实和诚恳的力量让我感同身受。注重特定诗意的画面营造,是志明作品的一个显见优点,也极易引发被雨淋的阅读共鸣和情感体验。但画面感的隐形缺憾在于,画面之外的东西隐藏少了,会阻碍文本的分歧之美;画面之外的东西隐藏多了,则会影响诗学的健康指数。志明的写作,遇水搭桥,见山开路,基本属于中规中矩的纸上耕耘,他享有“诗来找我”的礼遇,也乐见这份诗歌礼遇上升为自己的写作规则:笔下拒绝了时代的千军万马,所以就不再需要挥师渡江的雄心忐忑等待着肉眼可见的欲望安检。作为诗人,沂源也许已经像一个广袤的国度容得下志明所有的胜利和失败。我虽然时常未经志明许可而参与并分享他所贡献的被雨淋的感觉,但还是忍不住想提醒他——其实是提醒自己——长期陷入同一场雨淋并非诗歌的最佳结局,而追求最佳结局却始终是每一首诗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年之后仍然写作的诗人,与其说是兴趣所致,不如说是生命从生活中脱颖而出。奥登认为,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诗人,他首先是一个热爱语言的人。但在年轻的诗人身上,奥登发现,自己的观点常常变成这样: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诗人,他首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其实,语言难得有机会成为生活的直接成本,语言大于生活也好,语言小于生活也好,抑或语言和生活并辔而行也好,都是诗人的个体选择而不构成诗歌的主要问题。诗集《第六种果实》作为志明的中年之作,无疑是一次自主诞生,一份承前启后的证据——如果志明愿意,它可能就是志明睡眠时的枕头(已经很不错);如果志明不满足,它可能就是志明睡眠时的枕头随时被更新,被替换(还可以更不错)。兜了一圈回来,我的意思是说,中年之后仍然写作的诗人,既需要为语言担责,也需要为生命减负——就像海明威对生活的要求只有写作、打猎、钓鱼以及隐姓埋名,而隐姓埋名的前提却是你得有足够大的名声。生不为死,生即是死,中年恰是生死之间的豁然开朗:诗人,首先需要真诚地教育自己,然后才能有效地启迪读者。多么幸运啊,我读诗集《第六种果实》时,不止一次体会到了这个事实——每当感觉控制文本力不从心的时候,志明就会情不自禁地返回写作初心,通过心灵的自我矫正挽留中年写作的意义,使生命持续葆有了从生活中脱颖而出的力量:“像一个劫后余生的人/露出含泪的笑容”,又或者,“果实不论酸甜苦涩,都不会丢失/对老树的感恩。//并将照此轮回不休”。从一个纸上词汇到一种生命的过程,诗歌以其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美德消解了照此轮回不休的单一和沉重,这是诗集《第六种果实》的宿命,也是我愿意面对志明的新诗集说这么多题外话的间接原因。
多克托罗说,好的作品之于读者,不是正在下雨的事实,而是被雨淋的感觉——很早以前我读志明的作品,就曾体会过这种被雨淋的感觉。志明写有一首短诗《一个民工在打手机》,简陋的工棚里,一个年轻民工躺在简陋的小床上打电话,结尾是:“汗渍藏起了他的表情/机器的轰鸣掩盖了他的声音/我只看到两只伸出床外的大脚丫/像两只鸟,高兴地抖动”。如果我们没有去过深刻影响了生活的建筑工地,如果我们没有亲人朋友做建筑工人,就很难理解天地间抖动的两只大脚丫所蕴含的尘埃里的喜悦;同样,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份尘埃里的喜悦,也就很难参与到这首诗所生发的被雨淋的感觉。诸如此类的作品,志明写有不少,细心的阅读者在诗集《第六种果实》中也会常遇——《树荫悄悄出卖了他》《父亲拔草》《一棵开花的树》等诗作,就跟这种尘埃里的喜悦有着和光同尘、相互照应的关系。我有时审问自己,为什么对这种强调画面感的清晰之诗如此印象深刻,我想,不是它们承载的思想改变了我的阅读标准,而是诗人赋予它们的生活意趣以及由此产生的真实和诚恳的力量让我感同身受。注重特定诗意的画面营造,是志明作品的一个显见优点,也极易引发被雨淋的阅读共鸣和情感体验。但画面感的隐形缺憾在于,画面之外的东西隐藏少了,会阻碍文本的分歧之美;画面之外的东西隐藏多了,则会影响诗学的健康指数。志明的写作,遇水搭桥,见山开路,基本属于中规中矩的纸上耕耘,他享有“诗来找我”的礼遇,也乐见这份诗歌礼遇上升为自己的写作规则:笔下拒绝了时代的千军万马,所以就不再需要挥师渡江的雄心忐忑等待着肉眼可见的欲望安检。作为诗人,沂源也许已经像一个广袤的国度容得下志明所有的胜利和失败。我虽然时常未经志明许可而参与并分享他所贡献的被雨淋的感觉,但还是忍不住想提醒他——其实是提醒自己——长期陷入同一场雨淋并非诗歌的最佳结局,而追求最佳结局却始终是每一首诗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年之后仍然写作的诗人,与其说是兴趣所致,不如说是生命从生活中脱颖而出。奥登认为,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诗人,他首先是一个热爱语言的人。但在年轻的诗人身上,奥登发现,自己的观点常常变成这样: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诗人,他首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其实,语言难得有机会成为生活的直接成本,语言大于生活也好,语言小于生活也好,抑或语言和生活并辔而行也好,都是诗人的个体选择而不构成诗歌的主要问题。诗集《第六种果实》作为志明的中年之作,无疑是一次自主诞生,一份承前启后的证据——如果志明愿意,它可能就是志明睡眠时的枕头(已经很不错);如果志明不满足,它可能就是志明睡眠时的枕头随时被更新,被替换(还可以更不错)。兜了一圈回来,我的意思是说,中年之后仍然写作的诗人,既需要为语言担责,也需要为生命减负——就像海明威对生活的要求只有写作、打猎、钓鱼以及隐姓埋名,而隐姓埋名的前提却是你得有足够大的名声。生不为死,生即是死,中年恰是生死之间的豁然开朗:诗人,首先需要真诚地教育自己,然后才能有效地启迪读者。多么幸运啊,我读诗集《第六种果实》时,不止一次体会到了这个事实——每当感觉控制文本力不从心的时候,志明就会情不自禁地返回写作初心,通过心灵的自我矫正挽留中年写作的意义,使生命持续葆有了从生活中脱颖而出的力量:“像一个劫后余生的人/露出含泪的笑容”,又或者,“果实不论酸甜苦涩,都不会丢失/对老树的感恩。//并将照此轮回不休”。从一个纸上词汇到一种生命的过程,诗歌以其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美德消解了照此轮回不休的单一和沉重,这是诗集《第六种果实》的宿命,也是我愿意面对志明的新诗集说这么多题外话的间接原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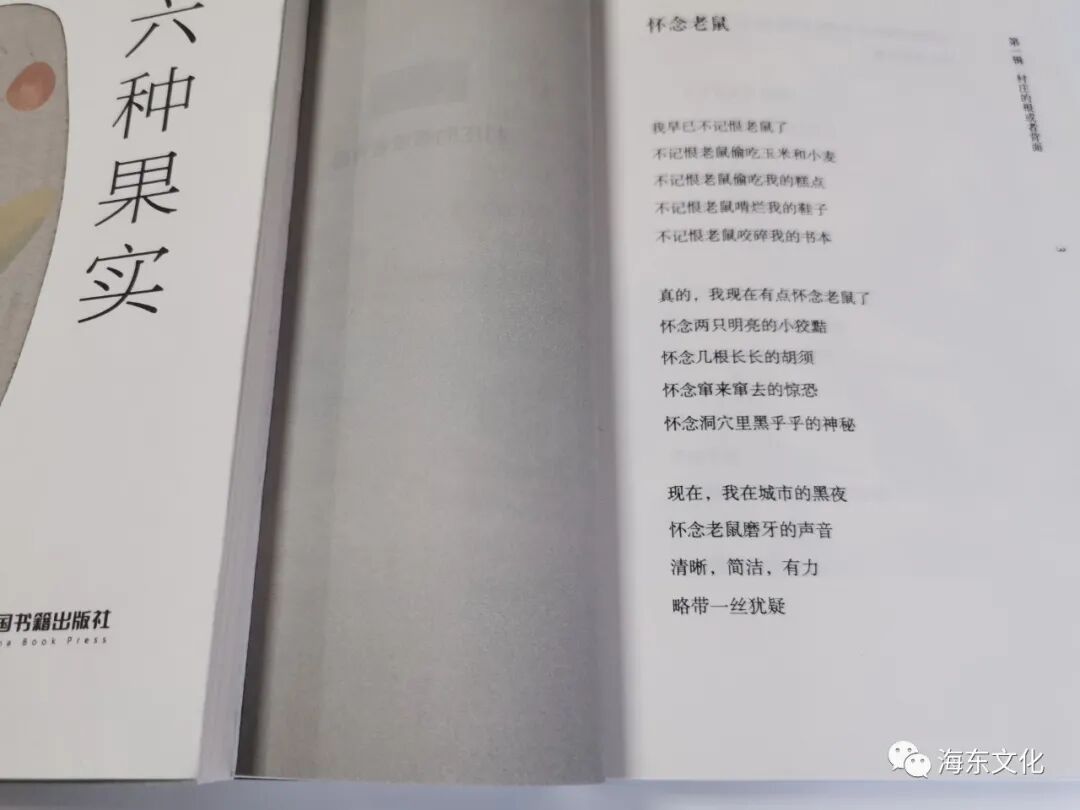 中国的诗人(也许不止中国的诗人),出版一本诗集充满冒险意味,原因有二:一是来自图书市场的直接威胁(购买诗集是一种比阅读诗集更为稀有的资源),二是来自诗歌文本的潜在风险(一些所谓的诗人,最容易被文本的集中呈现打回原形)。因此,合理面对一本诗集的现实存在,定义一本诗集的艺术尺度,冀望一本诗集可能的情怀涵盖和社会影响,既考验文本成色,更考验文本主人的境界——泯然众人之辈,在微信里热烈地兜售自己的诗集并且把作者签名作为噱头般的赠品(有多少喧哗迫不及待,就有多少尴尬敝帚自珍),他们一定没听说过这个故事:博尔赫斯先生从不在书房放置自己的任何作品,如果邮差送来作品的一个新译本,他会马上把它送给到访的客人,甚至就送给那位感到惊讶的邮差。事实就是这样,有些诗集无须检验,有些诗集有待检验,有些诗集从问世那一刻就丧失了检验的价值,始于叫卖,终于叫卖,沦为令诗歌蒙羞的社区花边新闻,无非一次俗不可耐的表演事故不值得稍加关注。在这个问题上,志明和我始终保持了足够的清醒,我们不想在诗歌那里成为被怜悯的对象,也没有在诗歌那里成为被怜悯的对象,为了这份自我加冕的个体诗歌尊严,志明和我曾经深入群山深处,喝了著名的沂源羊汤以示庆贺。在那里,我大声念了志明的一首诗,一首从诗集《第六种果实》中找不到的诗,献给高处,我叫不上名字的山峰;献给低处,我叫不上名字的河流;献给身边,我叫不上名字的羊汤馆老板和山清水秀的老板娘:“兄弟,有关秋天的柿子/我写过好几首诗了/每次都把枝头柿子比作小红灯笼/今天,我再次写秋天的柿子/什么比喻也不用/柿子就是柿子嘛/根本不是什么小红灯笼/不信你问问我家的小妹/她昨天在柿树林里收满一筐柿子/(爹说过,收完这些柿子/就去城里给她买件红面包服)/却没想到天会黑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啥也看不清了/她背着一筐柿子摸黑向山下走/那么多柿子没有一个发出亮光/照一照脚下的路/她一脚踩到悬崖下面/医生说她两条腿再也站不起来了/兄弟,你听了我讲的这些/你还能说柿子是小红灯笼吗?”现在,我把这首山峰听过、河流听过、羊汤馆老板和老板娘听过的诗抄录于此,结束我跟志明的这次纸上交流,并祝愿这本崭新的诗集在承担了第六种果实的虚拟责任以后,拥有一个原来如此的诗歌命运,替一只善良的羊、替一群善良的羊、替所有善良的羊深情回望一眼世间,感谢那些被比喻的青草在人类的胃口之外一直不肯老去。
中国的诗人(也许不止中国的诗人),出版一本诗集充满冒险意味,原因有二:一是来自图书市场的直接威胁(购买诗集是一种比阅读诗集更为稀有的资源),二是来自诗歌文本的潜在风险(一些所谓的诗人,最容易被文本的集中呈现打回原形)。因此,合理面对一本诗集的现实存在,定义一本诗集的艺术尺度,冀望一本诗集可能的情怀涵盖和社会影响,既考验文本成色,更考验文本主人的境界——泯然众人之辈,在微信里热烈地兜售自己的诗集并且把作者签名作为噱头般的赠品(有多少喧哗迫不及待,就有多少尴尬敝帚自珍),他们一定没听说过这个故事:博尔赫斯先生从不在书房放置自己的任何作品,如果邮差送来作品的一个新译本,他会马上把它送给到访的客人,甚至就送给那位感到惊讶的邮差。事实就是这样,有些诗集无须检验,有些诗集有待检验,有些诗集从问世那一刻就丧失了检验的价值,始于叫卖,终于叫卖,沦为令诗歌蒙羞的社区花边新闻,无非一次俗不可耐的表演事故不值得稍加关注。在这个问题上,志明和我始终保持了足够的清醒,我们不想在诗歌那里成为被怜悯的对象,也没有在诗歌那里成为被怜悯的对象,为了这份自我加冕的个体诗歌尊严,志明和我曾经深入群山深处,喝了著名的沂源羊汤以示庆贺。在那里,我大声念了志明的一首诗,一首从诗集《第六种果实》中找不到的诗,献给高处,我叫不上名字的山峰;献给低处,我叫不上名字的河流;献给身边,我叫不上名字的羊汤馆老板和山清水秀的老板娘:“兄弟,有关秋天的柿子/我写过好几首诗了/每次都把枝头柿子比作小红灯笼/今天,我再次写秋天的柿子/什么比喻也不用/柿子就是柿子嘛/根本不是什么小红灯笼/不信你问问我家的小妹/她昨天在柿树林里收满一筐柿子/(爹说过,收完这些柿子/就去城里给她买件红面包服)/却没想到天会黑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啥也看不清了/她背着一筐柿子摸黑向山下走/那么多柿子没有一个发出亮光/照一照脚下的路/她一脚踩到悬崖下面/医生说她两条腿再也站不起来了/兄弟,你听了我讲的这些/你还能说柿子是小红灯笼吗?”现在,我把这首山峰听过、河流听过、羊汤馆老板和老板娘听过的诗抄录于此,结束我跟志明的这次纸上交流,并祝愿这本崭新的诗集在承担了第六种果实的虚拟责任以后,拥有一个原来如此的诗歌命运,替一只善良的羊、替一群善良的羊、替所有善良的羊深情回望一眼世间,感谢那些被比喻的青草在人类的胃口之外一直不肯老去。 2020年9月,北京农展南里







李志明,山东沂源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散文》《十月》《北京文学》《中华散文》《山东文学》等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心旅》《流水穿过菜园》《幸福在玉米地里传递》《穿西装的土豆》及散文集《弯月镰刀》《无法藏起的时光》等。
